 |
《秋以為期》作家木子專訪
|
作家:木子
記者:淵懿
統籌:謝寧
責編:思展
時間:8 月 4 日晚 6 時
地點:香江資訊網 (土瓜灣道 94 號美華工業中心 A 座)

|

|
淵懿:木子小姐你好!很高興你能夠在百忙之中接受「香江資訊網」的專訪,恭喜你的中篇小說《秋以為期》正式與讀者見面!如果我沒有記錯,你的第一部作品是2017年出版的小說集《開到荼蘼》,第二本是2019年出版的散文集《遠去的風景,眼前的你》,現在推出的是第三本,短短5年時間推出三部作品,並且這三部作品都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大力支持,真是非常難得,可否談談這三部作品的創作素材和靈感是信手拈來,偶然得之,還是有一個水到渠成的自然成長過程?
木子:謝謝香江資訊網安排這次訪問,謝謝淵懿的採訪。我也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說說話。這三本書,第一本《開到荼蘼》是本短篇小說集。最近出的這本《秋以為期》是本中篇小說。這兩本書的素材都是一些聽來的故事,有的是身邊朋友講給我聽的,有的是一些新聞或者是一些八卦。這些故事,我先把它們打碎,然後組合拼裝,運用一些文學的表現方法,就變成了讀者現在看到的作品。至於散文集《遠去的風景,眼前的你》,是一本遊記,更多記錄了我的行走的腳步和心中所想。我想,作為一個喜歡寫作的人來講,素材的積累是一種慣性地收集,例如,我們今天的對談場景也有可能成為日後小說的一部分。所以,就我自己而言,等到時機成熟(這個時機,對我來說是有靈感,有閑情,有感觸或者特別想寫的時候。)就會有一個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地形成。 |
 |
淵懿:根據我的閱讀,中老年黃昏戀應該是解讀《秋以為期》這部中篇小說的多個面向之一。作為青年作家的你,是怎樣的機緣讓你產生以老年話題作為這部小說的創作主題呢?
木子:青年人的定義似乎一直在被刷新,所以你說我是青年作家,我也好高興。《秋以為期》是由一段婆媳關係引發的一個黃昏戀的故事,當中所探討的更多的是人,特別是女性,一個每日都在老去的女性,如何自處?如何面對人生的困境?至於,剛剛問起是怎樣的機緣,才會產生以老年話題作為小說創作的主題。那是因為有一個故事,是一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故事。我發現,我只要跳到其中一邊,就會站在這一邊的立場。這讓我詫異地發現,互相指責的一對似乎都沒有錯,那麼錯又在哪里?這些都引發了我的自我思考。之後,我開始多點留意社會老齡化問題,除了醫療、福利、社會生產力、經濟發展等,老年人的情感世界,也就是作為高等生物的人類必定會產生的感情,似乎也應該是社會需要關注的問題。 |
 |
淵懿: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文本中反復出現的藍色,甄珠的校服是藍色,甄珠學校的絨布是藍色,甄珠送男朋友的毛衣是藍色,肥仔花店的白色文化墻前面擺放的繡球花也是藍色……這個顏色的選擇是你的個人愛好,還是暗含著甚麽特別的意象表達呢?我突然想起張愛玲喜歡的顏色是「藍綠色」,我大膽猜測一下,這是否是你對喜歡作家在自己作品的投射或者致敬呢?
木子:藍色布校服是香港好幾間女子學校的校服,我很喜歡,覺得女生就應該是那個樣子。所以把它寫進小說。至於其他一系列的藍,也在這件藍布校服上產生的變換,都在表達女主角的孤獨、憂鬱、寂寞或者是品味。這當然是一種顏色的暗示手法,表達的情感也正如藍色本身所蘊含的情感。張愛玲確實是一位偉大的作家,我是看完她所有的作品。讀書時期的論文也寫過她,所以在寫作上受她影響,也是在所難免的。 |
 |
淵懿:《秋以為期》文本的細節描寫所佔篇幅特別大,有的片段甚至讓讀者感到「瑣碎」,但是就我個人的閱讀體驗,這樣的「瑣碎」不僅沒有形成閱讀障礙,反而在讀者腦海中構建出豐富而層次多維的畫面,進而有效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作為創作者,在文本中毫不吝嗇地鋪排細節是你一貫的創作風格?還是有其他考量呢?
木子:王國維說“一切景語皆情語” 指得是詩詞中所有景物都寄託有情思。強調情思要通過寫景表現出來,我是完全贊同,並將其運用在小說寫作中。我是這樣寫作的,跟著感覺寫,寫完了放在電腦裏,然後等到某一日,我再回過頭去檢視自己的文本。這個時候的我,是嚴肅和苛刻的,甚至是挑剔的,我不允許自己多一個沒有必要的字詞。所有留下來的,都是對文本的鋪墊和用於架構文本立體空間和氛圍。 |
 |
淵懿:我注意到《秋以為期》的女主甄珠常常和洗手間鏡子中的自己對話,這樣的情節鋪排,可以理解為作者是在強調女主的孤獨感呢?還是在借用鏡子內外一虛一實兩個甄珠,暗示與現實中柏林和肥仔的一個精神,一個物質的情感取捨?
木子:佛洛伊德認為人格結構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組成,這些人格特徵的描寫在小說中我做了一個鏡中人的安排。這是話劇或者電影中常常運用的手法,一虛一實,鏡裏鏡外的自我對話,總比老是寫:她想,她又想,來得有趣。我把寫作當作一個人的遊戲,任何方法我都喜歡去嘗試去佈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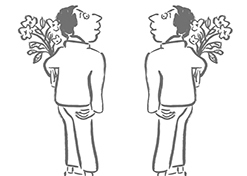 |
淵懿:我有一個猜測,文本對甄珠和柏林相戀的情節設置是要表達黃昏戀在精神層面的脆弱性,即使甄珠和柏林有相同的音樂愛好,也不能從柴米油鹽的人間煙火走出,而車禍情節的安排,就是象徵甄珠從精神死亡到現實物質的回歸,於是最後和肥仔的結合便是誰也難以逃脫的世俗婚姻圍城。如果給這場黃昏戀選一個顏色,我想選擇灰色,不知與你的文本預期是否契合?
木子:羅蘭·巴特著名的那句口號——作者已死。作者的想法,多半只能作為分析文學作品的參考而已,我們所有評論與解讀的依據,側重的還是「文本」,讀者藉由閱讀到的東西,再去思考它表現與表達了什麼樣的內容,去發現作品的新的意義,及形成一個新的創造性文本。所以,我在小說安排上,設定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尾,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觀點和角度,人生經歷的不同,為女主設定歸宿。小說出來後,我陸續收到十幾份讀後感,我很驚奇的發現,大家看到的真的都不一樣。所以,小說的顏色也會跟著讀者為其的定性而各自看到不同的顏色。如果一定要我為小說選顏色,就是封面的金秋。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起碼我希望自己是樂觀的,我心中所想的人生總應該是有希望和心生歡喜的。 |
 |
淵懿:我注意到女主甄珠在第三十四章節發生車禍,之後的敘述節奏明顯加快,描寫鋪排的細節也從之前的潑墨如水變得惜墨如金,從創作的角度,你是如何控制文本的敘述節奏呢?
木子:這個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寫作心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前輩談起創作,我說我在寫作的時候,眼前會出現畫面,他說他在寫作的時候是有音樂的。我回去,把他的話想了想。後來,我試著把這種聯想加入寫作中,我發現這是一種非常棒的技巧,作品的節奏會根據音樂的起伏自然而然地衍生和鋪排。但這方面,因為實在太抽象了,很難說一些很理論的東西,完全是很個人的感覺。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向您討教攝影技巧的時候,您跟我說過,拍照用光的重要性,我一直都記得。後來,我在看攝影作品時,發現有故事的作品,都是關於光和影的故事。所以,我在這本《秋以為期》中也嘗試運用了一些攝影的構圖。我的老師李默先生常說各種藝術是有共通性的,只有很好學習和感悟。才能夠讓自己得到提升。這方面,我是完全贊同的。 |
 |
淵懿:你在《秋以為期》的後記中寫道:「我把這許多個來自真實故事的原型打碎後,化成一個:『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的故事。」你能談談作為一個創作者,如何將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故事化作文學虛構中的真實,現實的真實和文學的真實二者之間的取捨裁剪是經過精妙的計算,還是跟著寫作的感覺和人物與情節的發展自然推進?
木子:『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我是被這首詞觸動,才會促使我寫下《秋以為期》這個故事。就像我在後記中所寫的,這個故事是個小故事,講得是普通人的普通事。這些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也就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故事,如果只是一個單純的記錄,是毫無意義而且毫不精彩的。所以,寫作必須對其進行取捨裁剪才會讓作品具有文學性。但同時這些故事的素材取自於生活,是人的故事,所以它肯定具有了真實性。
例如:《秋以為期》的每一個小說人物身上可能都有3,4個原型。主要是以目前的素材來講,單一的原型寫作,人物也不夠立體和豐滿,寫起來也會因為自己對原型的喜惡,而產生偏激。但是,小說人物不一樣,小說人物是藝術創造出來的。所以小說人物的生命力,是產生在故事的進展中的。
寫作的時候,感覺、人物與情節的發展自然推進都是需要的,除此之外,我還會多了一道修稿過程,這方面,我比較像花藝師,剪枝的過程毫不留情。在腦海中構造圖形,留下主要的線條。刪剪掉不必要的枝葉,營造空間感和氣氛。我想,我還是練習地不夠,等有一天可以一稿定型的話,那麼我就會對自己比較滿意。 |
 |
淵懿:談了很多有關你的大作《秋以為期》,我們跳開來說說香港的文化和文學吧。有人用莎士比亞說過的「三天可以出一個爆發戶,三年出不了一個貴族。」這句話來說明香港是個「文化沙漠」,另一種觀點又認為香港不僅是全亞洲教育水準最高的城市,還有金庸、倪匡、黃霑,蔡瀾「四大才子」,因此香港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大環境的沙漠,我知道你除了作家身份,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身份就是教科書總編,因此很想聽聽你對這個老話題的見解?
木子:一邊做編輯,一邊寫作的人,在香港文化界還是不少的。我自己覺得很幸運,因為可以做喜歡的工作,靠寫字賣文養活自己。香港是個中西文化交融,城市面貌又非常多元化的城市,這為寫作者提供了無限的創作空間和數不清的創作素材。從這一點上來講我不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雖然,香港沒有職業作家,您提到的(金庸、倪匡等前輩不屬於這代人,他們屬於紙本閱讀時代,那個時候是沒有手機干擾)但是,香港藝術發展局還是會對藝術創作提供一些資源,雖然很少,但也算是有的。從這一點上來講我也不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另外,香港的博物館和各種文藝表演也很多,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一定要讓自己學會找水喝的本領。
但同時,作為一個教科書編輯,我可能更看重一個城市的人文。人+文化才是一個現代文明城市的象徵。例如,我們出去旅遊,同樣是問路,不同城市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在一些小事情上,當地人給與外來人的,是幫助還是刁難?我也會留意公共洗手間是不是乾淨?地鐵上是不是排隊上車還是一擁而上?這些都是一個城市文化的象徵,而這些文化是由人體現出來的,這反而是我對我們這個城市是不是「文化沙漠」的判斷之一。
|
 |
淵懿:當下社會,在文化多元的衝擊下,我們不得不承認文學正在走向小眾和精英化,香港是個非常國際化,也非常物質化的城市,你對香港文學的未來持樂觀還是悲觀的態度呢?
木子:香港城市富裕,生活節奏快,甚至連地鐵的網路也特別快。僅有的碎片化的閱讀時間也被手機所佔領,這種大環境下,紙本閱讀者必定是不斷減少。文學也必將和其他藝術一樣,越來越小眾化。而且隨著元宇宙時代的到來,紙本閱讀者必將更加快速地減少,這些都很難讓人樂觀。但是,香港畢竟是香港,他有很多先天優勢,而且這一屆政府表示,要把香港打造成文化之都。所以或許我們都應該樂觀一點。 |
 |
淵懿:「香江資訊網」的很多粉絲都是文學愛好者,你對這些正在行走在文學道路上的朝聖者,有怎樣的寫作經驗分享或者推薦他們閱讀哪些作家的書籍呢?
木子:我其實也是在學習階段,我以前對書的選擇是只要看得下去,基本是什麼書都看。我現在有點變了,時間越來越少,看書變得挑剔。每一次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我是一定會看。我最近在看的是劉再複先生的《雙典批判》,是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去看《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還有,我開始看一些其他類型的書籍,主要以美學、設計、攝影為主。至於寫作經驗,我認為是要多寫多練,還有就是多學多交流,個人認為多學並不是單純地學習文學,而是多接觸不同的藝術,並學習觸類旁通。多交流是指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不用太多,二三個足夠,一起討論同一部作品,有點像以前的讀書小組,各自對書中的寫作手法說出觀點和角度,這樣才會有進步。 |
 |
淵懿:我感覺根據你目前的創作狀態,不久應該有一部長篇小說橫空出世。不知我的預感是否正確,或者說你已經開始構思新的作品?
木子: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沒有寫過長篇的作家,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一直想寫長篇,腦子裏一直在醞釀或者說蘊藏著一個長篇故事,但是正如我剛剛說的那樣,要有時間,靈感和觸動我坐下來寫得那個觸發點。我也在等那一天的到來。 |
 |
淵懿:期待你的第四部作品早日與讀者見面,並能在第一時間接受「香江資訊網」的專訪,如果你不反對我的邀約,就讓我們約定——「秋以為期」!再次感謝你!疫情反復,願你多多保重!多多創作!
木子:謝謝您的採訪,很高興和朋友們說說自己的小說和分享一些寫作心得。我也再次感謝「香江資訊網」的訪問。祝福「香江資訊網」讀者人數穩步上升。
|
 |
 |
國内讀者可通過專屬二維碼訂購 |

